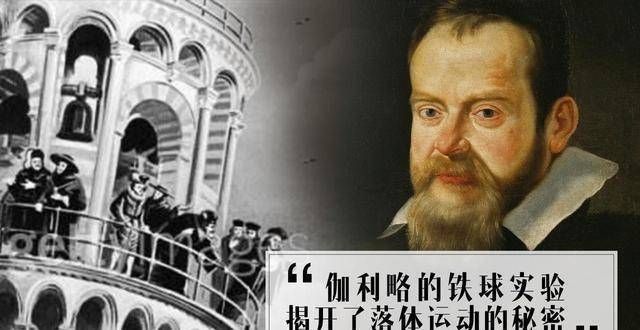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2006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现任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之所以提出重建,他藐视那些张口闭口都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崇古派。在崇古派看来,是因为当前的人文学术价值标准相当混乱,新近出现的某些的理论必定已经被一部《圣经》或《道德经》阐述过了——凡我们所知道的,甚至说已经有崩溃的趋势。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在当下学术界,古人早已知晓。在他们看来,我们很难判别一部(篇)学术成果的高下品质,古人总是神秘、伟大而又万能的。在培根生活的年代,以及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准。一般来说,就连伽利略都不敢直白地批评亚里士多德。然而培根却大胆地在《新工具》里写道: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同意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依赖于他人的权威;所以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人文学科评价虽然不像理工科那么明确,而说不上是同意。”
培根抨击亚里士多德,但在学术界内部,说他用逻辑学败坏了自然哲学,基本标尺还是很清晰的。然而现在却是相当混乱。说起来,导致信徒们对自然界充满了误解和妄断;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存在,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很多。就学术成果而论,是古代自然科学落后的一个原因。在培根看来,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奖励和项目评审,今人要比古人“高龄”,古人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懵懵懂懂、经验匮乏,他们偶尔画了几幅出色的涂鸦,却被看不懂的成年人拿来到处吹捧,这实在可笑;今人生活在古人之后,吸收了古人的经验、获得了古人的成果、避免了古人的覆辙,所以我们并无崇古之必要。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观念遭受古人的束缚,崇古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重大因素;伴随着它,迷信权威与服从世俗意见也发挥了消极作用,成为近代之前,科学思想无法取得重大发展的三大因素。
古人的思想里缺乏科学的成分
作为“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思想的基本缺陷——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单纯诉诸于思维和辩论,而未曾采用实验的手段。在培根看来,“事物究竟是否可解”这个问题不是通过辩论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实验来探究以及弄清楚它。例如对于光是否能分解的问题曾引发过广泛的辩论,有些人认为光是单颜色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多颜色,而只有牛顿不参与这种无谓的争论,他默默地把三菱镜掏了出来,将光谱投射给人们看。
但是,在古代这种重视实验的人非常之少。泰勒斯断言世界的本原是水,可他的依据仅仅在于自己观察到大多数事物的种子皆需要湿润来滋养,含有水分,所以水被当做了本原;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数是本原,因为他发现“万物皆可用数来说明”,所有事物都存在着数量,那么与其把本原归因于水、火、土,还不如归因于数。类似的,有人就编出了一个“道”、另一些人则胡诌一个“理”、另有“玄”、“虚”、“心”等各种繁多的名目。谁要是参与这种关于世界本原的争论,他将变为一位无所事事的清谈家,永远也得不出可靠的结论。原因就在于这些争论都只单纯诉诸于思维和辩论,而缺乏实验的验证。当泰勒斯与克拉赫利特争论世界是火做的而不是水做的、陆九渊对朱熹说宇宙是“吾心”而不是“天理”时,这些话的意义并不如“青菜比萝卜更好吃”多。
本原问题的争论是一个“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问题,永远也得不出结论
培根认为古人用逻辑之术来支撑自己的个人偏好,通过诡辩来确认“青菜比萝卜更好吃”这个主观结论,使之牢固而不容置疑。其中,亚里士多德就采用了这种做法,他的《工具论》在逻辑方面已为自然哲学定了型,“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例如,亚里士多德通过逻辑推论,巧妙地说明重的物体肯定比轻的物体掉落得快,因为重物的质量更大;同时他还说正圆是最完善的,所以星体必须绕着正圆轨道旋转。为了驳倒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他通过在逻辑方面揭露亚里士多德的自相矛盾,从而摧毁其理论。伽利略明确指出:
“亚里士多德使建筑学法则迁就他的宇宙构造,而不是使他的宇宙构造适应建筑学法则。”
“宇宙构造”是亚里士多德的个人主观偏好,他爱把宇宙说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然而宇宙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古代哲学家们喜欢对这些规律进行曲解,以便把它融入自己的“宇宙构造”中;很少有人能主动推翻自己的“宇宙构造”,承认建筑学法则的客观存在。所以,他们的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他们喜欢去争辩那些不能证伪的东西,却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最终使哲学变成“论道式”的清谈,而不是“实验式”的探索。
亚里士多德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自然,很少诉诸实验
要对哲学进行改革,使之科学化
古人的哲学讲究高深莫测,这样才能使信徒们崇拜敬仰,使他们虔诚心服而无意怀疑追问。欧洲中世纪的神父专研《圣经》,印度古代的僧侣讲论《吠舍》与佛典,魏晋时期的中国名士也喜欢辩论“三玄”。他们操着别人听不懂的术语,讲说着自己也无法验证的东西,却意识不到这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的内心在高深的精神世界中遨游,身体却摆脱不了日益黑暗的现实生活,那时的人民孱弱,国家四分五裂,到处都是生灵涂炭,而有人却在泥潭中向往天国、在饥饿时追求长生不死,这种愚昧的思想又谈何高深呢?
正因为古人的思想缺乏科学性,不懂得用实验来验证理论,所以培根把他们的旧哲学称为“人心的冒测”。要想复兴知识,就得改革哲学,把问题转向“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说他并不渴望在争辩中驳倒论敌,而是要在行动中征服自然,以此来得到准确的、可以论证的知识,从而实现哲学的科学化。
要想使哲学摆脱无用的逻辑争辩,成为可以验证的科学理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改造旧的逻辑思维方式,用科学归纳法来取代顿悟法。
古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基本都是顿悟法,他们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一下子就飞跃到最高的东西,并且将这最高的东西视为不可动摇的,并从中引出中级与低级的原理来。例如泰勒斯在感觉上察觉到大多数事物都含有水分,依赖于湿润,故而他一下子就飞跃到“水为万物之原”这个最高原理,然后再引申出“大地是安置在水上的”等次低级的原理。在这个思想体系中,缺乏从“大多数事物都含有水分”推导出“水为万物之原”的科学证明;又如,老子在生活经验中感知道路、水流、山谷等事物,然后他一下子就上升到“道”这个最高范畴,接着再引申出“柔弱胜刚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等次低级原理,同样是顿悟法。
不需要实验与积累,就声称自己顿悟出了最高的真理
对此,培根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归纳法。他要求理智从感觉经验出发,引出一些基本的低、中级原理,形成牢靠的底层基础,并且对其不断加以巩固;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无间断上升,达到或者达不到那个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的最高真理。顿悟法与科学归纳法都从经验、特殊的东西出发,都力求止息于最高、最普遍的真理;然而顿悟法对于经验、特殊的东西只投以匆匆一瞥,便迫不及待地要奔向自认为是最高的东西,它一下子就建立起某些抽象、无用又缺乏根据的原理。科学归纳法则是适当地按顺序贯注于经验的、特殊的事物,然后再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特征,逐渐上升到秩序、规律等普遍的原理去。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古人喜欢讨论普遍的东西,而对个体事物不感兴趣。他们说“道”是无所不包的,“神”就是一切,只关心“道”和“神”的各种属性,却对“道”所包含的东西、“神”所代表的事物毫不关心——神父对造物主认识得很通透,却对它所造出之物一无所知。他们可以高谈宇宙起源,却弄不明白彩虹形成的原理;可以像讲故事那样诉说天地造化生人的过程,却搞不懂人体的基本医理。培根认为自然界具有“精微”的特点,使得沉迷于抽象和普遍的古人认识不清它。
科学归纳法脚踏实地,不指望一下子就飞跃到最高真理
“冒测”思想使古人无法培养科学精神
古人精通于对宇宙、“道”和“神”的研究,然而他们就像自以为掘地就能冒出黄金的方术一样,实际上唯一的作用只是使土壤松动,便于后人耕耘而已。炼丹师的初衷并不是要发明,就如哥伦布往西航行的最初目标并不是找到美洲一样;古人的“冒测”确实能产生许多意外的发现,但这并不是他们有意为之,因为他们从未进行系统的实验。古人把自然当做一个谜语,不断地猜出许多答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荒谬绝伦的,只有少部分猜中了的谜底,才成为朴素的真理。而且人们普遍都存在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并不热衷于发现新的真理,而是喜欢把新的东西套入旧的体系中去,胡诌什么量子力学验证了《易经》;能量守恒符合佛教的六道轮回云云。
冒测者总是臭气相投,大多数人也喜欢接受冒测得来的结论,因为这些东西粗浅易懂,比那些科学的举证要有趣得多。冒测能够径直地促动人心的想象力,并以之来充当理解力——思考总是会疲劳的,而想象却是轻松的;所以解释的道理人们赖得去听,而冒测的传言他们却能听得津津有味。古代哲学家的活动范围始终没有超出地中海之外,却妄谈宇宙体系;他们不知道东方人,不接触美洲人,不了解黑人,却冒测人类之普遍本性,这实在是荒诞。
冒测的出发点本来就是错误的,它在科学方面永远也做不出什么重大进步。要想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就得从基础开始改造,而不是在旧理论上填填补补。培根的做法就是另辟蹊径,他将古人的哲学丢在了一边,不再去研究宇宙的起源、万物的本性,而是发明一种新哲学;这种哲学以人类的理智为对象,它研究理智的各种优点和缺陷,在探索自然的同时力求使理智避免受到各种假象的干扰,让其受到洗涤,以便进入科学的大门。
培根认为要用成果来评判学说体系,那些不出成果的清谈之论毫无价值,它们建立在意见之上,等到有影响力的祖师死去之后,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只有建立在科学之上的哲学体系才能绿树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