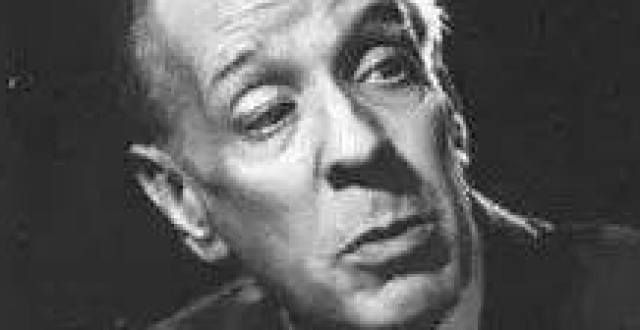
才智卓越者可以在清醒状态下,莫言以2150万的版税收入屈居“探花”。2014年,坠入意识中,第九届排行榜出来,清晰地梦见记忆深处隐藏的东西;觉醒者在朦胧中摸索,“状元”是张嘉佳(1950万),如于黎明未晓的路上前行,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陌生,只能模糊地眺望梦境的幻影;庸碌者没有梦。
博尔赫斯的主题是数之不尽的梦境与无限的宇宙,不过他的作品一说出来:哦,在梦中寻找真我、存在、永恒、荒谬、孤独。
读博尔赫斯,原来是他写的啊。张嘉佳的代表作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使我们在清醒中坠入梦境。
《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版的庄周梦蝶:“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这一年,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郑渊洁以1900万的版税屈居“探花”。小学肄业作家很少是以光头形象示人的,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好像就只有郑渊洁这独一份,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
人常常觉得过往清晰既定,未来善变模糊。
博尔赫斯观点亦如是:“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现的年份。”
年迈的他清醒地与过去谈话,但过去的他却无法真切地记住未来的自己。
这一篇章是博尔赫斯的自我剖析、反省自问,他直面回忆,如“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般,直面过去吸引自己的文学、隐喻、想象: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直面过去的博爱、宽容、虚伪。
它触发我的思考是:未来确实模糊善变,但过去是否真的清晰固定?
我们的思维总被固定的框架束缚:“生命是被一系列点串联的线,已经连接的点是不可变的,只有未来才充满可能性。”
但《沙之书》篇说到:“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假如我们的生命是“沙制的绳索”,过去的串联都是假象,触之即散,那过去是否也是模糊不定?
即,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是一个点,过去、未来、现在毫无关联,一切生命都如那本沙之书一般,无限无垠。
突然,将首篇《另一个人》与末章《沙之书》串联在一起,我开始明白:博尔赫斯在这几个篇章中探讨的,绝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散乱的过去,既定的过去,将一切规矩打乱后重组的过去,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过去也是不可捉摸的。
读至《事犹未了》中:“我一再对自己说时间是一条由过去、现在、将来、永恒和永不组成的无穷无尽的经线,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难以捉摸的了。那些深奥的思考丝毫不起作用。”
我更加确认这一点,于是,时间串联的线、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U字形状的外星生物、沙制的绳索,种种线状的物体在我脑海中层层纠葛,缠绕不清。
我试图将之抽离剥清,因而写了一段文字:
作家、画家、音乐家和众人站在湖边。
湖底遍布明珠,繁星般闪烁,众人注视着明珠,每颗珠子都内含乾坤,道道幻影,众人从中看到快乐、悲哀、恐惧、希望、情欲、堕落、超脱…
未几,众人迷失于繁星中,目眩神迷,不知所处何处,不知从何逃脱。
作家拾起一颗颗明珠,串成文字,诗篇重落入湖底,烨烨生辉。
画家串起珠子,编织出不同的形状,飞入天际,成了一个个星座。
音乐家也拾起珠子,谱成乐章,飘向远方,声乐悠扬。
众人才恍然惊醒,为之触动。
至此,人类有了诗歌、艺术、音乐,众人从规律中看到珠子内的喜乐悲哀,不至于迷失于无序。
再后来,越来越多卓越者从众人中迈出,串出不同的形状,人类终于意识到,浪漫是永无止尽的。
野蛮人看不到传教士手里的《圣经》,旅客看到的索具和海员看到的索具不是一回事。假如我们真的看到了宇宙,我们或许会了解它。
《沙之书》发表于1975年,此时的博尔赫斯已患上家族遗传的深度失明,因而在多篇短篇中都提到失明,尽管在文集中他强调失明并没有对自己造成困扰,但在现实中,眼疾却对他造成巨大的打击,50年代末期眼疾逐渐严重后,他便将所有的都转移到诗歌创作,一直到70年代才重新开始小说创作。
《沙之书》可以视为博尔赫斯晚年的回忆录,他曾说过自己从没写过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沙之书》也一如既往,在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中隐藏着时间、永恒、回忆、存在、幻象等主题,剖析自己的一生。
如前文三篇探讨的是自我、时间、追求,《乌尔里卡》中怀念曾经的恋人,以北欧传说《沃尔松萨迦》中的格拉姆剑,象征着情人之间相互渴望又相互防备,若即若离始终无法到神灵契合的孤独;《代表大会》怀念的是朋友、年轻的抱负、政见等等,最终化为永恒的瞬间;《阿韦利诺·阿雷东多》刻画一个沉稳犀利的刺客形象,喻示义无反顾的决然。
《阿韦利诺·阿雷东多》是《沙之书》文集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一篇,它体现了博尔赫斯的政见和革命意志,这种强烈的批判意志我仅在早期的《恶棍列传》中见到:
“我是红党,我自豪地宣布自己身份。我杀了总统,因为他出卖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同朋友和情人都断绝了往来,以免牵连他们;我不看报纸,以免人说我受谁唆使。这件正义之举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审判我吧。”
读此篇时,我仿佛在读鲁迅的《铸剑》,在我看来,《阿雷东多》塑造的刺客形象不逊色于《铸剑》塑造的眉间尺,在短短的篇幅中,体现了阿雷东多的孤独、厚重的情感、决然、悲哀、壮烈,透过阿雷东多,我看到另一个充满人性色彩的博尔赫斯。
《铸剑》中,复仇的眉间尺在闹市被围堵时,有段描写:“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
对阿雷东多的长相描写颇为相似,“他年纪二十出头,瘦削黝黑,身材要算矮的,动作有点笨拙。他的眼睛似乎睡眯眯的,但咄咄逼人,除此之外相貌十分平凡。”
小时候,我看不懂《铸剑》,后来才知道黑色人与眉间尺其实同为一人。
眉间尺天性软弱温柔,举棋不定,老鼠都不忍杀,闹市中被讹诈缺乏果断决行,欲复仇却心怀怯懦,黑色人果敢决然,智勇双全,是重生后的眉间尺。
阿雷东多身上同样具备柔和与果敢的两面性。
他平凡、少言寡语,他爱幻想,他渴望平稳快乐的生活,渴望飞瀑,山林,河流,怀念他曾爬到灯塔所在的山顶。
可是,一切他热爱的生活都已变了模样,乌拉圭广袤的土地在流血,他唯有拔捍卫一切。
阿雷东多象征着博尔赫斯坚持一生的反极权,他坚定地反对胡安·庇隆。他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
他认为:“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短篇集中,《代表大会》最包容万象,以我之见,这是博尔赫斯最佳的短篇之一。
那晚,他与恋人牵手走在路上,思考衰老与死亡。
他不知道人会在何时发现自己不复青春,以前他听过一句话:某天,你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不是你的妻子,而是一个略显老态的妇人,你才知道自己已然衰老。
他才意识到,衰老并非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瞬间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契机,在于人不再接受新的事物,转而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
“我并不为孤独感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物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
他突然理解《鼠疫》里那个反复倒腾鹰嘴豆的老人和《百年孤独》中晚年铸金的布恩迪亚上校,理解衰老是个什么东西。
那天,他看到年逾九旬的爷爷步履蹒跚,耳背膝软,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像晒稻谷般,把自己的一生铺开散落在太阳下。
他看着老人颤抖的嘴唇,浑浊的双眼,突然想知道即将死去是什么感觉。
走在农村破败的道路上,他看到每一栋破落残旧的旧屋子前都坐着一个老人,雕像一般,脸上刻着道道麻木的皱纹,散发着腐朽死亡的气味。他想起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坟场,老人是一座座行走的墓碑。
他转头对恋人说,我嗅到死亡的味道了,以前我总把死亡跟衰老区分开,因为我只考虑到早夭,且一度认为自己不会存活太久。衰老离我太遥远,可现在,我在太多人身上嗅到了衰老的味道,他们年纪轻轻,却活在巨大的坟场中,逐渐石化为墓碑。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
他对恋人说:写作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不至于快速消逝,甚至渴望不朽——“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写传世之作。”
《代表大会》的主题涉及种族、政治、战争、友情,我无意深究议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正吸引我的,是老人记忆里的议会,以及议会对记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
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拉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这是我惯来沉迷的瞬间即永恒,但那个“欢乐的长夜”对所有议会成员来说,似乎不仅仅是共有的记忆——宴会的篝火隐藏着熊熊燃烧的代表大会图书馆,成员们围着书籍的灰烬欢歌载舞,玫瑰、星辰、太阳、葡萄酒在他们脑海中飞速闪过,化为一帧帧永恒的碎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目,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
毁灭成了永恒的轮回——“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堂亚历山大为何要组建代表大会,为何要散尽家财,为何要焚毁一切——存在尽是混沌,代表大会是世界所有元素的集合,它永恒存在,个体的意识参与其中毫无意义,某一天人们被世界的本质吸引,试图探索它,最终发现文化、意识、存在都是荒谬,尽是轮回,个体的意志被世界的洪流裹挟,最肆意的欢愉就是在毁灭中寻找瞬间的价值,化为世界的一部分。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属于全世界。你们进来时经过这里,出去时还要经过这里。
我开始理解,极尽的美是属于世界的,但就如《镜子与面具》所言:“了解到美的罪孽,因为这是禁止人们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
感知到极尽美的途径,就是抛弃自我意识,没有孤独,没有痛苦,没有疑惑。在清醒中坠入梦境,融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无限宇宙的一粒尘埃——无止无尽本就是一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