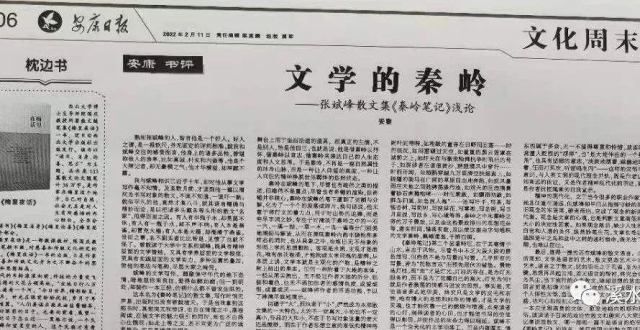
文学的秦岭
——张斌峰散文集《秦岭笔记》浅论
文||安黎
熟知张斌峰的人,一起加油!点击播放 GIF 0.0M,皆言他是一个好人。好人之谓,是一根软尺,并无固定的评判标准。就我和斌峰交往的感受而言,他身上的诸多品性,皆堪称做人的表率,比如真诚、朴实和内敛等。他是个大牌记者,却无豪横之气;他才华横溢,却深藏不露。
我与斌峰相识已近乎十年,却对他从事文学写作毫不知情。及至数月前,才读到他一篇以渭河为书写对象的散文。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貌似平凡的他,竟然才高八斗,就其语言精确与精妙而论,足以把诸多头戴各等头衔的散文“名家”,甩得百里之远。有人有半瓶子水,却晃荡不休;有人有一瓶子水,却不声不响;有人本是燕雀,却冒充大雁;有人本是大雁,却混淆于燕雀。世间之事,名不副实者比比皆是,见惯了也就不怪了。曾就读于大学中文系的斌峰,既具有精神层面的文学情结,又具有学养层面的文学根底,更具有实践层面的文学实力,多种因素的叠加,使他的笔法与笔韵,尽显大家之端倪。
斌峰的文学写作,颇像保守年代的地下恋情,暗地里你来我往,爱得如醉如痴;但一到明处,却装作一本正经,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似的。
这本名为《秦岭笔记》的散文集,写作时悄无声息,出版时也没有锣鼓喧天。于是当我拿到这部书时,甚觉突兀和惊讶,也自在情理之中。展卷阅读,在被文字的魅力吸引的同时,却也不由得心生慨叹:如此上等之文,若不向更为广泛的读者推介,实在是读者的损失。
《秦岭笔记》是一座用文字堆积起来的文学秦岭,山峦叠嶂,奇石嶙峋,草木森莽,云雾缭绕,鸟雀欢唱,就风光的多姿多彩而论,并不亚于真实的秦岭。
秦岭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热衷于吟咏的对象,近多年的散文写作者对其更是趋之若鹜。但纵观满目书写秦岭的篇章,大多似曾相识,沿着一种套路亦步亦趋,独具慧眼和独具匠心者,实在是寥寥无几。然而读《秦岭笔记》,却别有洞天,既养眼,又沐心,恍然间仿佛步入一个“风景这边独好”异域风情地带。在人人熟悉的地方,发掘出新意,再造出新景,生发出新论,这种能力,非庸常之人能够具备。斌峰“不走寻常路”的表现在于,他绕开了秦岭之大,而专写秦岭之小;对于秦岭,他不但有目之投入,更有心之融入。在相当程度上,秦岭并非他逐猎的终极目标,仅是他摆放在舞台上用于坐而论道的道具,而真正的主演,不是别人,恰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他是借秦岭以抒怀,借秦岭以言志,借秦岭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文思考。于是秦岭,不再是一座自然属性的冰冷山脉,而是一种让人仰望的高度,一种让人向往的精神挣脱世俗羁绊的悠然状态。
秦岭在斌峰的笔下,尽管也有雄伟之类的描述,但雄伟不是重点;尽管也有奇崛的渲染,但奇崛并非核心。秦岭在斌峰的笔下遭到了切割与分解,化为了一个个的段落或碎片。换句话说,他无意于将行文的着力点,用于对山势的追捧,而是穷尽字词之妙,专注于对掩映于秦岭之中的一石一穴、一溪一湖、一草一木、一鸟一雀等分门别类地捕捉与解读,从而在展现秦岭内韵丰饶性和多样态的同时,也从具象之中,冶炼出无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颗粒。客观是水流,主观才是浪花。唯有浪花卷涌,才能构成文学灵魂的澎湃。从本质上讲,文学本就是主观化的产物,是精神之树上结出的果实。任何一种附着于大地的客体,一经从笔尖流出,无不经过作者大脑的拆分、组装和着色,也无不添加作者的感度,或爱或恨,或喜或厌——斌峰将作者的再造功能,予以了淋漓尽致地演示。
回避于“大”,而执著于“小”,俨然成为本部散文集的一大特色。大的不一定真大,小的也不一定真小,作品的大和小,不在于书写对象体量的宏大还是微渺,而在于作者思想立意的高低和精神格局的宽窄。写大事件的,不一定是大作品;写小物件的,不一定是小作品。有人写小人物,却把自己写成了大人物;有人写大人物,却把自己写成了小人物。秦岭过于庞大,若笼而统之地书写,难免会掉入大而不当的陷阱,反倒给人的印象不是清晰而是模糊。于是斌峰像庖丁解牛那般,将秦岭予以解剖,将其局部的构成要件,逼真地予以呈现,从而让观者目睹得更为真切和透彻。
他写“雪的世界”;写“河流的足迹”;写“湖的绿”的“纯净”、“丰富”和“孤寂静谧”;写“浮萍”的“清清淡淡的微笑”;写“山永远都敞开自己的胸怀,接纳每一丝风雨,接纳每一个孤独的行者,接纳每一颗落寞的心”;写“石”的“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有的突兀地挺立,细而高;有的浑圆粗壮,像静默的大钟;有的层层堆叠似塔;有的团团相拥如浪”;写“天籁”的“声音时而清脆,如风铃在微风中摇曳,如山泉自高崖上落下,如百灵鸟在树叶间啼啭,如稚嫩的童音在田野间回荡……时而低沉,如闷雷碾过天空,如重重的黑云笼罩在城郭之上,如纤夫在与激流险滩抗争时吼出的号子,如跋涉者在滚滚黄沙、猎猎漠风中穿行……时而开阔,如鲲鹏穿越九万里清空扶摇直上,如脱缰的骏马在广阔的草原自由地奔跑,如疾风暴雨在天地之间驰骋荡涤污浊,如滔天的巨浪携裹着砂石奔腾咆哮……时而聚敛,如骤雨初歇,如群鸟归巢,如急流入海”……还写叶子,写茶,写银杏树,写刺树,写彼岸花,写雾凇,写老街,写日月星辰,写故乡,写心境等等。秦岭之中和秦岭之旁的万千景致,以及由这些景致悟出的思想花朵等,虚实相间,错落有致,足以使这座由字句堆积的文学秦岭,巍峨逶迤,千娇百媚。
《秦岭笔记》第二个显著特征,在于其寄情于山水,言志于风物。尽管书中不乏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但绝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几乎所有的写景,皆为“托物言志”而预先埋伏的铺垫。景物是灯柱,而“志”才是灯光。灯柱的存在,是为灯光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高大。灯光为何?就是作者激荡的情感与迸发的思想。事实是,无论语言多么地华美,终究只是文学的皮毛和衣饰,唯有博大的思想和纯净的情感,才是文学的灵魂,也才能依靠一己的燃烧与喷涌,点亮读者的心灯,润泽读者的心田,也才能使书写的价值得以彰显,并使作品的生命力得以绵延。斌峰不是一个空壳化的文学油漆工,而是内蕴厚实、情感饱满和思考深邃的文学内行,他把自己对万事万物的思考,把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的爱憎,都依托于景致来曝光。景致是他的唇舌,是他心灵的展板。在他瀑布般流泻的言说里,情感宛若滔浪飞溅,思想仿佛光泽熠熠闪烁。最为擅长也是最为醒目之处在于,他赋予景致以生命,将其人格化,于是无论雪雨,无论草木,无论山石,无论花鸟,无论街巷,仿佛都有了心思,有了秘密,有了情绪,有了急于倾诉的强烈意愿。如此,主体和客体,就相互置换,如胶似漆地搅拌在了一起,难分彼此,让人无法真正厘清究竟是谁在替谁代言。客观物事大量的拟人化,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而且从侧面透映着作者无比鲜明的价值和道德取舍。作者的思维,属于天空,而不属于笼子,不以世俗的偏见为己见,不以既定的结论为己论,并以人性的视觉,以人文的观念,“重估一切价值”。在作者的笔下,世间无一样东西属于多余,无一不值得尊重和怜惜,就连时常遭人贬损的“浮萍”,也“是大地伸出的一个触角”,也具有坚韧的意志,“淡淡地漂着,幽幽地绿着,任雨打风吹,听雷鸣电闪”——这样的觉悟与意识,与人类文明的现代理念并轨,既是作者认知高远的佐证,又是作者精神现代化的明证,更是作者抗拒绳索的自我宣示。
精神的现代化,之于当今很多的职业作家,尚且任重而道远,但斌峰却早已从抱残守缺的陈旧观念的牢笼里,破壳而出,完成了观念的新陈代谢。观念是文章的心魂,也是判断文章高低和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观念落后,缺少人性的自觉和人道的关怀,纵然妙笔生花,文章也难以逃脱笼中之鸟和盆中之树的速朽宿命,既无法飞翔,也难以茁壮。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斌峰的散文语言。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更是艺术中的艺术。语言之于散文,犹如羽毛之于孔雀,至为关键。思想再风起云涌,若无语言的帮衬,终究会化为风尘。当下流行的众多散文,除却思想的贫血,语言更是枯燥无味,此等病症的形成,皆因作者个人悟性太低,造诣太浅,磨砺太少,而又欲望过盛,功利心和投机心过于严重,最终致使散文这一本应优雅高贵的文体,愈发地趋向粗粝和鄙俗。读读诸子百家的政论性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记事说理散文,哪一部哪一篇不是语言的绝唱?《秦岭笔记》的语言,就目前国内的散文现状而言,用鹤立鸡群来比拟并不显得虚夸。凝练,温润,隽永,精妙而雅致,蓬勃而鲜活,一股浓浓的诗意,犹如缥缈的云雾,将整个文本覆盖。于是阅读文章,始终给人以小羊啃食嫩草的清新与翠绿之感,草叶上的露珠,仿佛能将人心打湿。尤其是随处可遇的各种修辞,比如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交错使用,更使文章如四月的山野,红绿相间,铺排成漫无边际的花海。排比,呈海浪涌之势;比喻,更是妙趣横生;拟人,直接拉近了读者与客体之间的距离,似乎在阅读时,能感知到所写对象的呼吸,聆听到其心灵的密语。
张斌峰的文学才情是不用怀疑的,加之他数十年的丰厚阅历,以及土坷垃般朴实的心怀,于是他才能像十年磨一剑的隐士那样,剑一出鞘,就锋锐无比。我坚信,只要他持之以恒地磨砺,脚踏实地地迈进,在书写中注入更多的烟火之气,更大的成功,一定会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原文刊发在2022年2月11日《安康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