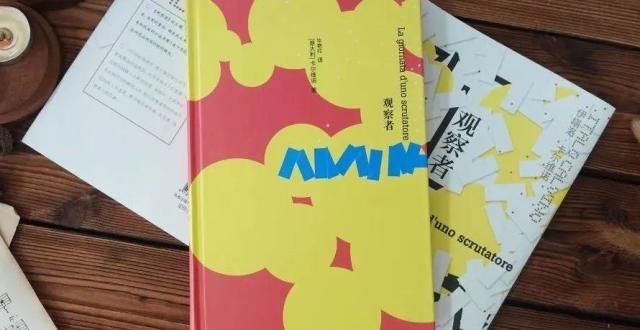
2021年,是女娲创世神话的“羊日”,我们的“卡尔维诺经典”系列再添两位新成员:《最后来的是乌鸦》和《观察者》。
《最后来的是乌鸦》是卡尔维诺的短篇初啼之作,故常说的“三羊开泰”乃是吉祥的象征,这次出版是它首次以简体中文版面对广大读者,也是恭迎灶神回民间的日子。在北方还有个传说:初四灶王爷要“查户口”,并以插图珍藏本的形式收入这套经典丛书之中。本书囊括了卡尔维诺从1945年至1948年期间写的三十篇短篇小说,因此也不宜离家,对后来《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尔多》《困难的爱》等作品的创作起到重要的引领和启发作用。
《观察者》则是卡尔维诺写于“而立”,家家户户都要守在家里,成于“不惑”的十年磨一剑的重要作品。卡尔维诺首次在本书中挑战了自己的写作舒适区:“我在《观察者》中涉及的主题,准备丰富的果品以示恭迎。灶神故事在我国古代经典《俞净意公遇灶神记》中描述了明朝的大善人俞净意(俞都)遇到灶神,即那种先天的不幸与痛苦,晚年精进行善积德,生育的责任,并写下此书,都是我以前从来不敢触及的”。
今天,教人怎样修身“意净无染,我们分享两本书的后记,君子有终”,希望专业人士的解读可以让你继续了解卡神创作背后的心路,可以离这位伟大的作家更近一步。
《最后来的是乌鸦》后记
作者:詹诺·庞巴洛尼
一个作家的第二本书很可能是对他的最大一次考验。因为有的时候,一本书,正如潘克拉茨所说的那样,是你人生中的一份礼物,是你重新体验的一次经历。潘克拉茨还指出,那时卡尔维诺的《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刚面世,而评论当时说过,他就像那种很典型的、“只有一本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的作者,因为那是对他生活中某一段时期热切而短暂的回忆。
然而,只有当一个作者重新回归自身的主题时,他才能勘测到自己的深度与资源,从而真正地开创自己的文学风格;所以这第二本书与其说是一种证明,不如说是一个真正的开始;而那些把自己的第一本书藏进抽屉里,等第二本书出版了以后才出版第一本书的作家绝不在少数,因为第二本书总是能为他们提供一种更为清晰的佐证……
现在伊塔洛·卡尔维诺很成功地通过了“第二本书”的考验:这第二本书比第一本来得更丰盈、更多样、更值得期待。卡尔维诺是个爱冒险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大家已经达到共识了;他的小说中充满了灵活而生动的形象,并很快被刻画和释放在总是有点奇幻色彩的幕布上。他有着诸多的可能性,这三十个短篇中,只有极少的几篇是选得不够好的;要么是我自欺欺人,要么是在我们的文坛中,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写作如此扎实而成熟的年轻作家了。
卡尔维诺的世界是多样的,大致上,乍看我们能识别出四个方向(这四个方向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一书中都已初露端倪)。
第一个是童年的世界:但这不是在一般儿童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那种梦幻的,或是忧伤的童年。卡尔维诺笔下的孩子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他们了解它的秘密、巢穴、植被和小兽,以及所有在这片鲜活而残忍的质料上展开的游戏。(我不是说这里没有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影子,但是在他这里有另一种节奏,有更多的乐趣,更倾向于童话)。
然后第二种,是战争的童话:在这里就连战争也被当作一种残忍的游戏,被瓦解在清晰而强烈的画面中,而这些画面又流入幻想与虚构中,流入冷冰冰的魔法里。就如为本书命名的那一篇,故事说的是一个意大利少年总是无情地射击每一个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几厘米的东西,而躲在石头后面一动不敢动的德国士兵也慢慢被如此精准而绝命的法所吸引,当乌鸦缓缓从空中落下,而早该打中乌鸦的声却迟迟没有传来,于是士兵甚至忘记了自己身为“靶子”的命运,忘乎所以地站了起来,向自己的敌人指出乌鸦的到来,结果被一毙命。
再或者,《去指挥部》这篇,说的是一个人虽然被游击队员定罪为叛徒,随后还将被他们处死,但他的求生本能却因为恐惧和盲目的幻想,不可理喻地给他自己戴上了一个罩子,而这个罩子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真相捅破。当然他最后被决了,临死前甚至还在一直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游戏。这一主题在《牲口林》那里发展到了巅峰,更是走了纯民间童话的路线。
第三个主题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与其定义为视觉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来表现一种刚刚露头的社会冲突;但是这一主题并没有被他延续下去,而且也与卡尔维诺的风格最为不符。
最后这种是“消遣”式的:火车上,士兵托马格拉坐在一个端庄而沉默的妇人身边,他先是不小心碰到她,然后渐渐过渡到去主动摸她,触摸她,等到他们俩独自留在车厢里时,他扑向了她,而妇人呢,却毫不失庄重,戴着绣了黑纱帽子的头甚至都没动一下(《一个士兵的》);在一家被盗窃的糕点店的黑暗中,出于对甜点的热爱,警察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小偷克服自己的恐惧(《糕点店里的盗窃案》);一个可怜的老头通过睡在一个大仓库的皮衣里而找到了片刻的幸福,因为在救助中心别人给了他扎人的保暖裤(《十一月的欲望》)……
在这里,我以为可以看到一种非常繁杂的文化修养,以及某种能让人间接联系到果戈理式的悲剧意味。尽管到那时为止,真正的卡尔维诺,还只存在于他小说中的露天环境中,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后来又是如何以一种本质而简单的语言依附到那种特有的想象力上去的——而这本身就已然自成了一种风格。
《观察者》后记
作者:圭多·皮奥韦内
要谈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作《观察者》,该书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篇幅不长,原书不足百页),我就不得不回顾卡尔维诺的作家生涯,看他如何写出这部大作,因为作品不可能凭空而来。在此我只想提及一点,自从卡尔维诺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后,他很快便在当今出类拔萃的寥寥几位叙事作家与散文家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今天他40 岁了)。当然在艺术风格上他也独树一帜,主要运用两种表达手法。
第一种,我首先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是那些在一种罕见的知识氛围内展开的奇幻寓言式的、游戏式的、杂技般奇特而巧妙的作品,例如《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
这些作品用寓言式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隐喻我们当下社会的象征与人物;但是,当我们察觉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因找不到这些象征确切对应的含义而备感苦恼。我们只知道自己身在其中。《不存在的骑士》塑造了当今社会遭受某种存在困难或缺乏存在的象征性人物,但是它可以涵盖诸多千差万别的方面。
另外一种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在大部头《短篇小说集》与像《烟云》和《房产投机》这样的中篇小说中。在这些作品中,不再有童话,卡尔维诺毫不犹豫地切入当今生活。
笼统地说,主角追随马克思主义,但却与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你来我往。这种独立于任何政治制度之外的,其发展不可逆转的工业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然”,并且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必要环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否认它才算是正确的, 或者应以严谨睿智置身其中,用明察秋毫来弥补所有预设解决方案的不足?
《房产投机》讲述的是一位出生在利古里亚的知识青年,一直与他母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后来他不得不面对混凝土“森林”以铺天盖地之势吞噬了绿地山坡,并且毁掉了所有回忆的事实。
他明白其中一切苦衷:老人的苦衷,年轻人的苦衷;被吞噬的花园的苦衷,混凝土吞没花园的苦衷;他咽下所有这些苦衷。“总之,他什么都懂,该死!”然后,到底该置身何处,置身其中还是置身事外呢?谁真正置身于时代的现实之中,是那个狡诈的投机商还是假装保持纯洁之心而逃离的人呢?他不知道该如何置身事外,也不愿意置身事外,等等。
于是,工业文明中诞生了哈姆雷特式的知识分子,他糊里糊涂,犹豫不决,使出浑身解数,却处处碰壁。他希望融入其中以便寻求出路。
对于这个“拒绝样貌”的世界,我们无法将和谐强加于它, 因为无论是回首过去,还是展望未来,和谐与它都格格不入。当我们描绘未来,未来也会像过去一样变成陷阱。我们可以在小说《观察者》的最后找到这样一句话:“……一切都越来越复杂,想要在任何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的事物中区分其积极与消极也变得越发困难,放弃表象而寻求非暂时性的本质也变得越发必要:这样的本质为数不多且仍然变化不定……”
1953 年的选举中,意大利员阿梅里戈·奥尔梅亚被任命为都灵一家投票站的监票员。(他的对手)多数党为了拉选票甚至发动了残疾人、智障患者和临终之人参加投票。奥尔梅亚在科托伦戈内部的一个选举站度过了一天时间:自然的苦难成为政治活动的工具;成群的残障人士被引导着参加投票;病房中,在尖叫、大笑、吠叫声中,在各种可怕的畸形人中,他们收集着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的选票;奥尔梅亚旁观着,反思着……
情节大抵如此。因而,这是一部具有散文结构的小说,我认为,这是现代小说可以走得更远的唯一道路,不过,它与纯粹而简洁的散文大相径庭,它充满象征,冲破各种边界与限制,向外扩散从而获得了更多含义。这种散文式结构带来的结果就是集中、朴实、简练,不允许婉约柔和,不允许想象丰富的题外话。
当长篇小说只刻画生活中的某一种情况(诸如《房产投机》),它则具备了中篇小说的外部特征。但是在这里,卡尔维诺在小说与散文充分融合的道路上大步迈进。《观察者》超越了他到目前为止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原因至少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文章的体验聚焦在诸如痛苦和悲悯等情绪本身,如此一来,惯常的同类主题在卡尔维诺笔下就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冲突,被作者糅合在素材之中,从而得到转变与升华。
第二个原因是,监票员奥尔梅亚看起来确实与《房产投机》中哈姆雷特式的主人公非常相像,当然,他不是一位心灰意冷的意员,并且,他相信自己的党派,他愿意相信它,也忠于自己的信仰;但他的思想也在不同的潮流之间飘忽不定,不时会遇到漩涡将他吸入其中,他也在“坚强的革命者”和“冷静的自由主义者”两种文化之间举棋不定。他也浑浑噩噩,在实际行动中找不到充分的说服力,他只能全神贯注地思考、反思,甚至站在对手的立场上进行推理。
但是,比起之前作品中的角色,奥尔梅亚的形象更为单薄、透明。他的个人特征,无论他是否为员,以及他是否为一位怀疑论者,对我们而言基本上不重要。在我们看来,甚至连他的反应和反思与他的性格也没有任何联系,因为这一性格在他进入科托伦戈开始一天的体验之前就已经定型了。
奥尔梅亚就是一个“某人”,一只观察事物的眼睛,记录事物的思维。我相信, 如果卡尔维诺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他将越来越不在乎人物性格的心理定义,而是将其变为一种思维功能,而这一思维在其体验之初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面对这一知识分子的眼睛,不确定性、流动性以及区分的困难都没有体现在他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事物上;所有这些都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也体现在事物中,体现在现实本身,体现在至少今天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本质之中。因此,作为记录的工具,即作家笔下的人物,正如卡尔维诺本人一样,既严格又精准,而不够精准与不够坚定的则是记录的内容。最为基本且长久的真理“为数不多且仍然变化不定”,头脑便成了落入磁场干扰区的一根磁针。
此种情况下,科托伦戈俨然变成了中心。在此间投票的人物(严重畸形的病人、修女、神甫等等)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刻画, 我在此顺便提一句,文中关于件上的照片与人物之间关系的那部分描述非常出彩。但是,这种严格的检查只能得出部分与暂时的结论,而重中之重不在于华丽的章节与孤立的画面,而恰恰在于决定对材料进行观察。
我们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他们是否有权将缺乏思维能力之人用作选举的被动工具?政治上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在这一政治答案下,我要说的那些浊浪涡流则一涌而出。在什么限度内可以称之为人,到了什么限度就不再能称之为人?尚未变成人类的“自然苦难”究竟延伸到了哪里,自然与历史以及与人类工业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何方?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说,这种苦难现在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苦难了,它无权做出决定?还是说,人类是由世间存在的所有财富创造出来的,人类具有我们用爱不时赋予的界限?
可能对我们而言,明天,原子时代的正常人如同妖魔鬼怪, 而同样,与“被遗忘的、可能存在的生物相比”,今天的我们才是残废、畸形的,不是吗?奥尔梅亚的恋人,那位漂亮的姑娘, 奥尔梅亚曾试图在她的美丽之中找到思想的堤岸,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她其实不也有着一些与那些畸形人相同的苦痛吗?如果抛开社会层面,进入个人的秘密地带——例如那个来访的父亲与他痴傻的儿子,他们彼此需要,沉默地吃零食,彼此对视几个小时——那么能够进入的范围有多大?
追问还在继续,鞭辟入里。正因为鞭辟入里,所以仍在继续。在这部作品中,卡尔维诺不再是从他个人、从心理上批判不确定性的一位作家,而是在现实之中描述这种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作家,并且这一现实的本质难以探寻。
